年的形状是什么?我捉摸不透。
小学时候看见课本里的插画,那些“大头娃娃”穿得姹紫嫣红,放着鞭炮的场面仍印在我的脑海中。然而我一点也不喜欢那幅画,倒不如说,小学课本里的所有插画我都不大喜欢,既不可爱也不漂亮。
背诵过“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”这种诗,看着春节期间的街道染上了红色,超市里人潮拥挤买年货……春节不就是这个样子?
突然发现,我一点也不喜欢春节,不喜欢过年。
每年的春节诸如上述那样,纵使能收到些压岁钱小礼物什么的,我也基本提不起劲。我家里也没有很强的家庭和家族观念,除了非常亲近的那几位,我家几乎不去走亲戚。看着同学朋友们讲述春节走亲戚收了多少红包,我虽羡慕,但这份羡慕中应是少有“想要变成那样”的心情。即使拿到了那么多压岁钱,我也没有地方要用。没有需求,也就没有想要获取的心情了。
不对,不走亲戚只是我上了初中高中之后的事情。在这之前我家还没有搬家,与祖辈的联系很频繁。那时的过年,七大姑八大姨都会来联系,我也会去他们家做客。一群人聚在一起看屏幕不大的CRT电视机,磕着瓜子聊天,到了晚上或许还会在他们家里住下。
随着搬家、升学,联系就明显减少了。再后来祖辈的离世,围绕着他们的链子就逐渐生锈、断裂了。过年的规模阵势,也就小了很多。
过年从此变得寂寞了起来。
请不要误会,我并不是想回到从前那个过年的氛围。我认为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的过年氛围,都是不错的。
我本就与那些亲戚不熟悉。在我的观念里,“羁绊”这种东西是实打实的,不是依靠着“亲戚”或者“朋友的朋友”这样的头衔就能建立。所以说,见不到他们反倒还更轻松,毕竟谁想跟一群“陌生人”度过节日呢?
但是有一丝落寞无处安放。
除夕前一日去给逝世的奶奶烧纸钱,本想给她说一句新年快乐,但怕被旁边的父亲责骂,就作罢了。况且死人也不会听见我的声音。
而且祭奠悼念的时候允许说这样的话吗?我不知道。但是,想祝她新年快乐的心情是真实的。
传说每逢除夕,有一年,“年兽”跑到一村作恶,被一家门口晾的大红色衣服吓跑;到了另一村,又被灯光吓走;到了另一处,也被打扫的人吓跑。于是,人们开始了解“年兽”的弱点,它怕声音、怕红色、怕火光、也不喜欢整洁的环境,所以每至年末岁首,人们就在家门口大扫除、贴红联、放鞭炮、挂红灯,又在院子里烧柴禾、拢旺火,用菜刀剁菜肉来发出声音,以吓走“年兽”。
人们庆幸打败“年兽”,于是敲锣打鼓,互称“恭喜”,便是“过年”一词的由来。
突然间想入非非。年兽几千年都如此,也该对红色和响声产生免疫了吧。说不定,人家年兽早就不怕这些,不吃人类这一套了。
正好现在的人们大多也不放烟花炮竹了。
除夕夜,年兽来到了一家人门前,本想作恶,攻其不备。却发现人们忙着瓜分百亿红包,通过一种不可视的网联系起来。屋里电视中春晚的声音式微。
年兽惶恐地回到街上,却发现每个人都在这张网上,团结得不像人类,却丝毫听不见爆竹声响看不见春联艳红。被这股无形的压力所迫,年兽灰溜溜地逃走了。
这是后来人类中广为流传的佳话。
年也听到了这则故事,它说确有此事,自己的确在没见到红色没听到响声地情况下离开了。
但绝不是逃走。
况且,它也已经不再畏惧爆竹和红色。
想必,是人类已经不再惦记提防着它。
年兽,获得了一丝无处安放的落寞吧。
来自遥远的时光、逝世的亲人、禁燃的烟火、袅袅的炊烟。
我从没并且再也见不到那个在除夕夜降临人间的凶恶猛兽。或许年,根本长得不凶恶也说不定。
年的形状是什么?我捉摸不透。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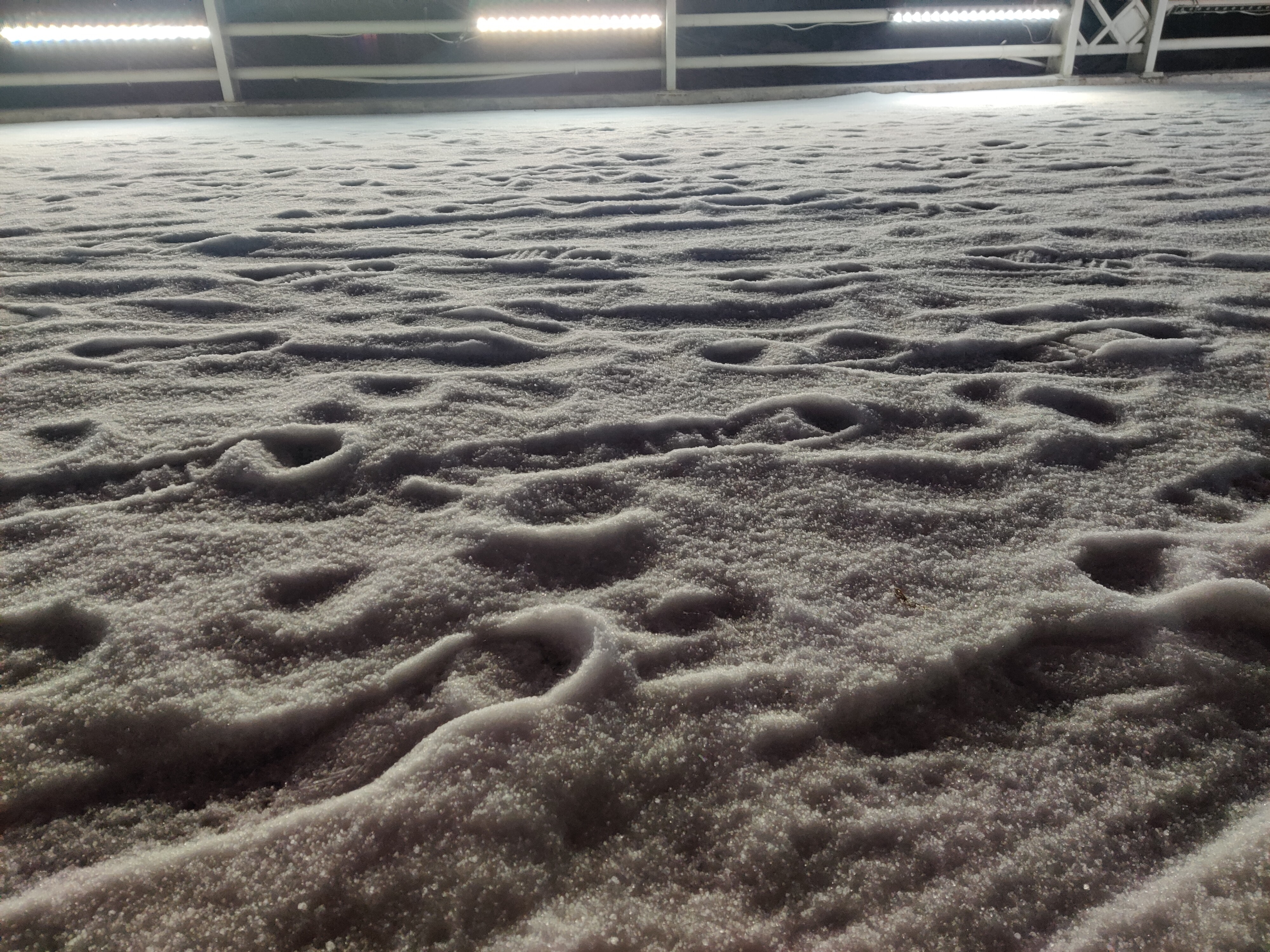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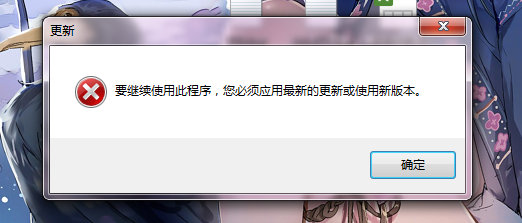

越长大年越没味道了,小时候和小伙伴玩鞭炮能玩到大半夜,春晚也守着看,去年不让放鞭炮了感觉年过的太没感觉了,甚至春晚什么的除了小品也懒得看了,小时候春节的快乐是能玩,现在春节的快乐只是能放假了
说起来,我家也好多年没放鞭炮了。往年春节会出去旅游,这两年由于疫情也哪都去不了。现在回想起从前,已经恍如隔世了π_π
还是小时候好,过年无忧无虑的。那会对什么都好奇,感觉还有些年味,现在过年除了拜个年、领个红包,跟平常几乎没什么区别
所以只要活着,世界就会慢慢变得无趣 (不是
(不是
年是什么形状的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吧。
的确如此。我曾赋予年一个形状,但渐渐地发现我期待的并非这样。
所以我捉摸不透∠( ᐛ 」∠)_
说起年兽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赛尔号年兽…
童年回忆XD
我没怎么玩过赛尔号啦
随便写写
rua